
近日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在《中國能源報》高調表態:“我是一個太陽能派”。難得一見省級領導的坦蕩敢言和對光伏事業如此堅定,筆者不禁感嘆:光伏幸甚!山西幸甚!感慨之余,一些想法不禁躍然筆下:
“我認為,太陽能是一個新興產業,一個朝陽產業,一個永恒的產業”袁書記如是說。作為一個光伏產業研究人員,筆者為一位高級領導人有這樣的認知而高興。是的,相信有太陽的存在,才有人類的存在,太陽的能量是無限的也是低成本的,成為人類的主要能源只是技術問題、時間問題。如果中國的各級政府都是如此懂得光伏,合理推動光伏產業發展,中國真正成為全球新能源強國之日可待。
在西方國家,就算國家元首呼吁支持光伏,反對派、立法體系如果不支持,支持的力度一定是有限的;中國則不同,各級政府確實擁有著極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是可以辦大事的。因為如此,各級政府更應慎用這份權利,過去中國光伏產業發展中政府好心辦壞事的例子比比皆是。
說起山西,人們在想到煤海的同時自然也想到嚴重的污染,也想到全省煤炭資源整合后大量民間資本的投向問題,更想到山西產業格局重構問題。對此,袁書記說“之所以要發展太陽能,對山西來講,是一個優勢變兩個優勢”。充分發揮山西特有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加速產業結構轉型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科學合理的發展光伏產業不失為一個聰明的選擇。
但是,山西的光伏產業發展之路應當如何走卻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發展模式的選擇無疑事關重大,發展模式的種類可以多種多樣,山西應當尋求一種新的光伏產業發展模式。
中國的光伏產業版圖基本是由以江蘇為代表的光伏產品加工基地和以青海為代表的大型光伏電站建設基地兩大模式構成的。已有的模式,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自然條件下形成的,未必是最合理的模式、終極模式,事實上江蘇和青海還在試圖調整。光伏產業的發展模式還在發展之中,未來也一定是多種多樣的,特別是在中央強調“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今天。
試著解讀袁書記的一席話,山西是想探討江蘇和青海二者結合的發展模式:“利用煤的優勢發電,發展電以后搞太陽能芯片,做出芯片之后再搞太陽能發電”。事實上,前年底山西省政府策劃郭臺銘、朱共山這加工和原料生產兩大巨頭考察山西光伏產業就已經在嘗試之中。這種發展模式簡單看有其合理之處,但在現實中卻是有待探討的。
值得探討的原因之一,是目前全球范圍內光伏產品加工能力已經處于嚴重供大于求局面,中國更是重災區。袁書記所說的:“太陽能過剩是出口過剩而不是使用過剩”是不成立的,因為“使用”是需要國家巨額補貼的,目前各國的補貼都已經或正在捉襟見肘之中,中國更是如此,據此,全球已有的60GW組件產能足以滿足人類一段時間的發展需求。
值得探討的原因之二,是總體看山西建設光伏電站的日照條件并非最好。即便如袁書記所說的“比如山西右玉縣,它一年光照時間有2800個小時”也比青海格爾木3500小時相去甚遠,更何況海拔高度決定的日照透視條件更是無法相比。
更值得探討的是,山西能否改變在中國只要提及經濟發展總是難以跳出實體經濟和規模經濟的慣性思維。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新的經濟形態不斷涌現,服務產業的貢獻值日益提高。山西歷史上以“票號”為代表的金融業有過輝煌的過去,今天從煤炭礦產中退出的民間資本擁有雄厚的財力。光伏作為規模經濟的能源產業形態,它的發展是建立在海量的融資需求和對金融產品不斷創新的基礎之上的。探討多種形式的金融服務,打造中國新能源產業的融資中心,山西具備提供這種服務的可能。從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看,美國以成熟的金融手段影響各國經濟的現實值得思考。筆者更相信,隨著立足全國的山西光伏產業服務環境的建立和完善,袁書記所希望的當地光伏實體產業也勢所必然因運而生。
(作者為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光伏研究員、光伏研究中心主任)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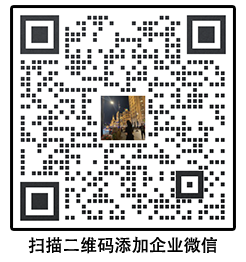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