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煤炭價格從2011年年底開始的大幅下跌,大部分省份的標桿上網(wǎng)電價在最近都實現(xiàn)了1.5分錢左右的下調(diào),但對應于可再生能源補貼的增加以及其他環(huán)保措施支出的增加,終端銷售電價仍舊保持不變。也就是說,上網(wǎng)電價的下調(diào),實體經(jīng)濟并未從能源成本中獲益。對于處在電力上游、價格低谷的煤炭行業(yè)而言,電價下降帶來的潛在需求也還無法兌現(xiàn)。
2013年初開始實施的新的煤電聯(lián)動辦法,將煤價變化5%作為調(diào)價的觸發(fā)條件,而“年度為周期”在現(xiàn)實操作中也被解釋為“以自然年為周期”,也就是整年才進行調(diào)整。這一過長的調(diào)價周期可能在未來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
僅就2013年煤價變化而言,從年初到現(xiàn)在,各地區(qū)煤價的下降幅度普遍在20%-30%之間,考慮到煤炭占電力成本的80%左右,以及300克標煤左右的效率水平,電價需要下調(diào)6分-1毛錢。扣除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調(diào)價幅度,未來的電價仍舊需要一次性的下調(diào)5-8分錢。這種下調(diào),應該充分的體現(xiàn)在終端銷售電價當中。
下調(diào)電價,是電價機制的應有動作。
電價下調(diào)具有必要性
目前我國的電價水平已經(jīng)不低,居民與企業(yè)的支出負擔急需減輕。這個事實的基本邏輯在于:價格作為標桿價值的信號,其高低只有相對水平才有意義。
從消費者的負擔來講,比較能源價格的高低,需要以收入水平為基準。我國消費者的收入只有歐美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而電價與歐美已在同一量級水平,導致能源支出擠壓了其他消費性支出,成為我國居民福利水平上升的一大負擔。
從工商業(yè)的能源負擔而言,可貿(mào)易部門需要參與全球競爭。從基于匯率轉(zhuǎn)換的角度,我國目前的工商業(yè)電價已經(jīng)比美國高出30%—40%,比亞洲鄰國韓國也高出不少,由此帶來的競爭力下降是明顯的。
從終端售價所包含稅率的高低,可以比較不同政府對能源消費課稅的程度,反映出各個政府的政策意圖或目標。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實行高達30%-50%稅率政策。從生產(chǎn)者的效率來講,不含稅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生產(chǎn)者可以獲得的收入,相應的成本如果可比較的話,這一不含稅價格就反映了市場的設(shè)計要素與生產(chǎn)者的效率。
電價下調(diào),對于降低用電企業(yè)與居民的用電負擔是立竿見影的。如果政府認為我國實施低的電價水平是與“節(jié)約能源”、“環(huán)保”相矛盾,可以就此機會通過提高稅收水平予以糾正,將這部分稅收建立“綠色支持賬戶”,取得提高競爭力與支持綠色發(fā)展的雙重紅利。
忌憚“高耗能”反彈是誤導
鋼鐵、化工、有色等通常所指的高耗能產(chǎn)業(yè),一直是各項公共政策限制的重點。從根本上講,對高耗能產(chǎn)業(yè)的限制是基于其環(huán)境的負外部性,這一問題的解決有賴于環(huán)境標準的提高與執(zhí)行的剛性。事實上,高耗能并不具有“原罪”。
退一步講,即便限制高耗能是一個“好”的政策目標,基于忌憚高耗能反彈而反對下調(diào)電價的觀點仍具有誤導性,這屬于混淆了“機制”與“手段”。電價應是一種機制,內(nèi)生于上游煤炭的成本及其他因素變化。如果高耗能被認定具有負的發(fā)展外部性,需要通過抬高其面臨的電價限制其發(fā)展,那么加稅抬高其能源成本屬于局部政策手段的范疇,而不應 “投鼠忌器”,去限制一般性的整體經(jīng)濟機制發(fā)揮作用。
過去,限制高耗能發(fā)展的電價政策叫做“懲罰性電價”,沒有做到電價機制與政策工具的有效區(qū)分,其多收的“電費”賬戶的去向,是否補貼了由于高耗能而受損的群體,也有待進一步透明。這些都是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
電價交叉補貼可一同取消
過去,我國的居民電價低于工商業(yè)電價,這一“交叉補貼”幅度在出臺階梯電價之后有所下降。這種制度安排并沒有降低居民的實際支出總負擔,因為工商業(yè)的高昂電價必然要傳導到居民的各種消費品。與此同時,其誤導了居民用戶的電力消費行為,無助于居民用電的節(jié)約。這一制度的唯一好處,在于對于收入最低階層的實質(zhì)性補貼。這部分用戶需要從“暗補“變?yōu)?ldquo;明補”,以保證政策的總體效果是累進的。
但是總體上,取消交叉補貼是建設(shè)統(tǒng)一市場的要求。如果居民總體電價水平上漲50%,可以進一步降低工商業(yè)電價10%。這樣,我國的工商業(yè)電價水平將大體處于美國的水平。這一政策變化,將對居民電力消費信號指引具有象征意義,對工商業(yè)競爭力提也具實質(zhì)性意義。
(作者系IEA全球能源展望組高級研究員)
2013年初開始實施的新的煤電聯(lián)動辦法,將煤價變化5%作為調(diào)價的觸發(fā)條件,而“年度為周期”在現(xiàn)實操作中也被解釋為“以自然年為周期”,也就是整年才進行調(diào)整。這一過長的調(diào)價周期可能在未來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
僅就2013年煤價變化而言,從年初到現(xiàn)在,各地區(qū)煤價的下降幅度普遍在20%-30%之間,考慮到煤炭占電力成本的80%左右,以及300克標煤左右的效率水平,電價需要下調(diào)6分-1毛錢。扣除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調(diào)價幅度,未來的電價仍舊需要一次性的下調(diào)5-8分錢。這種下調(diào),應該充分的體現(xiàn)在終端銷售電價當中。
下調(diào)電價,是電價機制的應有動作。
電價下調(diào)具有必要性
目前我國的電價水平已經(jīng)不低,居民與企業(yè)的支出負擔急需減輕。這個事實的基本邏輯在于:價格作為標桿價值的信號,其高低只有相對水平才有意義。
從消費者的負擔來講,比較能源價格的高低,需要以收入水平為基準。我國消費者的收入只有歐美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而電價與歐美已在同一量級水平,導致能源支出擠壓了其他消費性支出,成為我國居民福利水平上升的一大負擔。
從工商業(yè)的能源負擔而言,可貿(mào)易部門需要參與全球競爭。從基于匯率轉(zhuǎn)換的角度,我國目前的工商業(yè)電價已經(jīng)比美國高出30%—40%,比亞洲鄰國韓國也高出不少,由此帶來的競爭力下降是明顯的。
從終端售價所包含稅率的高低,可以比較不同政府對能源消費課稅的程度,反映出各個政府的政策意圖或目標。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實行高達30%-50%稅率政策。從生產(chǎn)者的效率來講,不含稅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生產(chǎn)者可以獲得的收入,相應的成本如果可比較的話,這一不含稅價格就反映了市場的設(shè)計要素與生產(chǎn)者的效率。
電價下調(diào),對于降低用電企業(yè)與居民的用電負擔是立竿見影的。如果政府認為我國實施低的電價水平是與“節(jié)約能源”、“環(huán)保”相矛盾,可以就此機會通過提高稅收水平予以糾正,將這部分稅收建立“綠色支持賬戶”,取得提高競爭力與支持綠色發(fā)展的雙重紅利。
忌憚“高耗能”反彈是誤導
鋼鐵、化工、有色等通常所指的高耗能產(chǎn)業(yè),一直是各項公共政策限制的重點。從根本上講,對高耗能產(chǎn)業(yè)的限制是基于其環(huán)境的負外部性,這一問題的解決有賴于環(huán)境標準的提高與執(zhí)行的剛性。事實上,高耗能并不具有“原罪”。
退一步講,即便限制高耗能是一個“好”的政策目標,基于忌憚高耗能反彈而反對下調(diào)電價的觀點仍具有誤導性,這屬于混淆了“機制”與“手段”。電價應是一種機制,內(nèi)生于上游煤炭的成本及其他因素變化。如果高耗能被認定具有負的發(fā)展外部性,需要通過抬高其面臨的電價限制其發(fā)展,那么加稅抬高其能源成本屬于局部政策手段的范疇,而不應 “投鼠忌器”,去限制一般性的整體經(jīng)濟機制發(fā)揮作用。
過去,限制高耗能發(fā)展的電價政策叫做“懲罰性電價”,沒有做到電價機制與政策工具的有效區(qū)分,其多收的“電費”賬戶的去向,是否補貼了由于高耗能而受損的群體,也有待進一步透明。這些都是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
電價交叉補貼可一同取消
過去,我國的居民電價低于工商業(yè)電價,這一“交叉補貼”幅度在出臺階梯電價之后有所下降。這種制度安排并沒有降低居民的實際支出總負擔,因為工商業(yè)的高昂電價必然要傳導到居民的各種消費品。與此同時,其誤導了居民用戶的電力消費行為,無助于居民用電的節(jié)約。這一制度的唯一好處,在于對于收入最低階層的實質(zhì)性補貼。這部分用戶需要從“暗補“變?yōu)?ldquo;明補”,以保證政策的總體效果是累進的。
但是總體上,取消交叉補貼是建設(shè)統(tǒng)一市場的要求。如果居民總體電價水平上漲50%,可以進一步降低工商業(yè)電價10%。這樣,我國的工商業(yè)電價水平將大體處于美國的水平。這一政策變化,將對居民電力消費信號指引具有象征意義,對工商業(yè)競爭力提也具實質(zhì)性意義。
(作者系IEA全球能源展望組高級研究員)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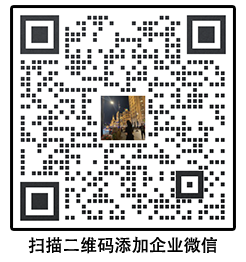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