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多晶硅企業技術與產能的突破,“兩頭在外”中的原材料這一頭,已基本得以解決。而終端應用方面,雖已有起色,但與龐大的產能相比,仍有很大的距離。
諸如“產能過剩”、“價格戰”、“雙反”等形象,無疑正是對這種產業失衡發展的一種懲罰,只不過因金融危機的催化提前爆發而已。隨著大眾媒體對此頻頻報道,中國光伏行業的負面形象被進一步固化和加劇,繼污染形象之后,再遭一系列負面“標簽化”形象危機。
補貼非議
在光伏行業的發展歷程中,始終脫離不開一個背景,即政府補貼。但有意思的是,現今的光伏行業,一方面在享受著政府補貼,一方面卻又遭受著過剩的煎熬。在整個行業面臨產能嚴重過剩、全行業虧損的大背景下,國內一些光伏企業卻仍在獲得高額的補貼,這難免不被輿論非議。
而地方政府的補貼名目,也可謂是“花樣繁多”。比如備受質疑的地方政府對海潤光伏的補貼,其中既有徐霞客鎮政府以新興產業首次超百億企業獎勵的4800 萬元,又有江陰市關于企業成功上市的財政獎勵1000 萬元人民幣及關于人才引進資金補貼4000 萬元人民幣。
綜合來看,許多人對海潤光伏獲得的補貼主要有兩點質疑,一是補貼的時機,此次補貼發放正處在歐盟對中國光伏企業“雙反”調查之際,這無疑于是授人口實,給對方調查提供最直接的證據;二是海潤光伏在上市時,其大股東曾作出業績承諾,而在該公司現有業績已經明顯低于承諾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補貼無疑是在用納稅人的錢替企業履行業績承諾。
客觀而論,財政補貼并非光伏行業獨有。但光伏行業的補貼之所以飽受詬病,背后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即相應的補貼并沒有換來應有的環境改善。
在一些人看來,雖然國外也給予光伏行業大量補貼,但起碼獲得了清潔能源的應用和發展。反觀國內,受各種因素的制約,每年高額的財政補貼并未換來多少環境改善。而一些以增加就業和拉動經濟為角度的辯解理由,與這一行業外的人又有多大的關系呢?
轉變跡象
光伏行業的負面形象,已非行業自身力量所能解決。但對個體企業而言,如果想獲得社會的認可,減少相應的非議,通過開發相應的產品或途徑與更多普通人的生活產生交集,無疑是較好的破解方式。
從現有的一些信息來看,相關政策制定方也正在開始轉變思維,由原來的對個體企業的直接補助,轉向對應用終端的補貼。
安徽省合肥市近日就表示,將以光伏應用推廣為抓手,不斷完善標準、政策、規劃、宣傳四大支撐體系,努力建成“中國光伏應用第一城”。
而來自江蘇省發改委的信息也顯示,該省今年將力爭光伏并網容量超過200MW,用戶側并網自發自用容量超過600MW。并正著手建設分布式光伏發電規模化應用示范區,無錫、南京等8 個城市的實施方案已上報國家能源局,申報項目規模超過1500MW。
出臺類似措施的地區還包括另一光伏大省——江西,該省財政日前投入8000 萬元資金,專項用于獎勵2012 年光伏產品推廣與產業發展應用示范項目。
不過,其中也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如一些地方政府仍在對市場進入設置一定的前置條件,輕則要求在本地注冊、納稅,重則要求采購本地企業產品。
無疑,這仍然是在重蹈覆轍。
而在更高層面的產業政策方面,有媒體報道稱,工信部正會同相關部委加緊推進涉及光伏制造業各環節的準入條件,準入“門檻”主要涉及三大“準繩”——技術研發實力、環保水平和產能規模。其中,在技術研發方面,將嚴格執行“高新技術年銷售收入5000 萬元以下,研發投入須達6%;銷售收入為5000 萬-2 億元的企業,研發占比須達4%”等規定,以促進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在生產規模方面,如電池生產環節未來產能規模均需達100 兆瓦以上;在環保標準方面,將在電耗水平以及相關環節產生的廢液、廢氣排放等多方面提出明確上限。
有業內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按照上述報道信息來看,雖然較以往有所改變——比如將研發投入作為一個指標,無疑有助于鼓勵企業通過技術來進行差異化競爭而不是單純的價格戰——但仍然延續了對生產規模的要求。而據以往經驗來看,這能否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還是越調產能越高,尚需拭目以待。
諸如“產能過剩”、“價格戰”、“雙反”等形象,無疑正是對這種產業失衡發展的一種懲罰,只不過因金融危機的催化提前爆發而已。隨著大眾媒體對此頻頻報道,中國光伏行業的負面形象被進一步固化和加劇,繼污染形象之后,再遭一系列負面“標簽化”形象危機。
補貼非議
在光伏行業的發展歷程中,始終脫離不開一個背景,即政府補貼。但有意思的是,現今的光伏行業,一方面在享受著政府補貼,一方面卻又遭受著過剩的煎熬。在整個行業面臨產能嚴重過剩、全行業虧損的大背景下,國內一些光伏企業卻仍在獲得高額的補貼,這難免不被輿論非議。
而地方政府的補貼名目,也可謂是“花樣繁多”。比如備受質疑的地方政府對海潤光伏的補貼,其中既有徐霞客鎮政府以新興產業首次超百億企業獎勵的4800 萬元,又有江陰市關于企業成功上市的財政獎勵1000 萬元人民幣及關于人才引進資金補貼4000 萬元人民幣。
綜合來看,許多人對海潤光伏獲得的補貼主要有兩點質疑,一是補貼的時機,此次補貼發放正處在歐盟對中國光伏企業“雙反”調查之際,這無疑于是授人口實,給對方調查提供最直接的證據;二是海潤光伏在上市時,其大股東曾作出業績承諾,而在該公司現有業績已經明顯低于承諾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補貼無疑是在用納稅人的錢替企業履行業績承諾。
客觀而論,財政補貼并非光伏行業獨有。但光伏行業的補貼之所以飽受詬病,背后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即相應的補貼并沒有換來應有的環境改善。
在一些人看來,雖然國外也給予光伏行業大量補貼,但起碼獲得了清潔能源的應用和發展。反觀國內,受各種因素的制約,每年高額的財政補貼并未換來多少環境改善。而一些以增加就業和拉動經濟為角度的辯解理由,與這一行業外的人又有多大的關系呢?
轉變跡象
光伏行業的負面形象,已非行業自身力量所能解決。但對個體企業而言,如果想獲得社會的認可,減少相應的非議,通過開發相應的產品或途徑與更多普通人的生活產生交集,無疑是較好的破解方式。
從現有的一些信息來看,相關政策制定方也正在開始轉變思維,由原來的對個體企業的直接補助,轉向對應用終端的補貼。
安徽省合肥市近日就表示,將以光伏應用推廣為抓手,不斷完善標準、政策、規劃、宣傳四大支撐體系,努力建成“中國光伏應用第一城”。
而來自江蘇省發改委的信息也顯示,該省今年將力爭光伏并網容量超過200MW,用戶側并網自發自用容量超過600MW。并正著手建設分布式光伏發電規模化應用示范區,無錫、南京等8 個城市的實施方案已上報國家能源局,申報項目規模超過1500MW。
出臺類似措施的地區還包括另一光伏大省——江西,該省財政日前投入8000 萬元資金,專項用于獎勵2012 年光伏產品推廣與產業發展應用示范項目。
不過,其中也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如一些地方政府仍在對市場進入設置一定的前置條件,輕則要求在本地注冊、納稅,重則要求采購本地企業產品。
無疑,這仍然是在重蹈覆轍。
而在更高層面的產業政策方面,有媒體報道稱,工信部正會同相關部委加緊推進涉及光伏制造業各環節的準入條件,準入“門檻”主要涉及三大“準繩”——技術研發實力、環保水平和產能規模。其中,在技術研發方面,將嚴格執行“高新技術年銷售收入5000 萬元以下,研發投入須達6%;銷售收入為5000 萬-2 億元的企業,研發占比須達4%”等規定,以促進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在生產規模方面,如電池生產環節未來產能規模均需達100 兆瓦以上;在環保標準方面,將在電耗水平以及相關環節產生的廢液、廢氣排放等多方面提出明確上限。
有業內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按照上述報道信息來看,雖然較以往有所改變——比如將研發投入作為一個指標,無疑有助于鼓勵企業通過技術來進行差異化競爭而不是單純的價格戰——但仍然延續了對生產規模的要求。而據以往經驗來看,這能否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還是越調產能越高,尚需拭目以待。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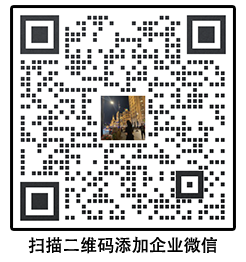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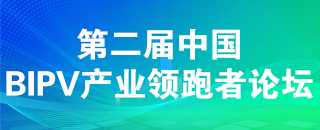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