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亞洲規模最大煤化工企業——安徽臨渙焦化股份公司生產廠區內,工人在煉焦爐上忙碌。C FP圖片
如果棄風棄光問題不能盡快解決,可再生能源行業將整體陷入惡性循環,而且我國承諾的減排目標都可能會落空。
———中國風能協會秘書長秦海巖
179個污染天,其中46天重度污染———這是北京市環保局公布的2015年北京天氣狀況。2015年入冬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出現了三次大范圍重污染天氣。12月,環保部緊急向12個省級人民政府印發預警通知,要求啟動應急響應,最大程度減輕污染危害。隨后,全國共有15個城市先后啟動重污染天氣紅色預警,預警級別和范圍均超以往。
根據環保部的研判和總結,煤炭的使用依舊是霧霾的第一大來源。
2015年,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不僅用電需求疲軟,煤炭價格也一直不見起色。但是,產業鏈末端的煤電行業寄托著拉動煤炭消費的熱望和各地GDP的期待,在一個市場化程度不足的電網系統中依然堅守著優勢地位。這時候,很多人也開始熱議———為什么霧霾如此嚴重,能源結構卻這么難調整,可再生的風電、光伏和水電更是大量被棄之不用,造成巨大的浪費?
與減排承諾背道而馳
火電“瘋狂上馬”,“棄風棄光”大面積出現
“中國不僅承受著氣候變化的巨大影響,也面臨著環境污染的嚴峻形勢。因此,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生活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不是別人逼著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就迫切要做的事情。”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在巴黎氣候大會“基礎四國”的發布會上說。
為證明責任感與決心,在巴黎談判的會前和會中,各國元首、部長們紛紛向全世界宣布了各自國家的減排方案。各國已經有了這樣一個共識:導致全球氣候迅速變化的溫室氣體增量主要是由工業化進程中化石能源的使用造成的,因此來一場“能源革命”,大幅度調整能源結構,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最核心的手段。同時,不論是電煤、散燒煤,還是汽車尾氣———這些反復被論證為“霧霾元兇”的,并且在排名先后問題上被爭論得熱火朝天的關鍵詞,也全都是來源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因此,對正處于工業化快速進程中的中國而言,“能源革命”又有了第二層意義———那就是向迫在眉睫的環境污染宣戰。
然而,2015年11月到12月間,各地大面積出現“棄風棄光”的現象。中國風能協會秘書長秦海巖對南都記者說:“這就顯得匪夷所思了———法律規定要保障可再生能源優先上網,全額收購,可到現實中怎么卻處處是反著來的呢?”
他告訴南都記者,去年以來,由于電力的產能過剩以及火電瘋狂上馬,棄風棄光問題越發嚴重。尤其是入冬以來,甘肅、寧夏、黑龍江等地區的棄風棄光比例超過60%,有的地方甚至勒令可再生能源機組停發。全年的棄風棄光電量接近500億千瓦時,直接電費損失近300億元。其中棄風電量可能達400億千瓦時,相當于去年新增風電裝機的全年發電量。也就是說,風電產業一年的新增社會經濟效益全部被浪費了。
他擔心,如果棄風棄光問題不能盡快解決,可再生能源行業將整體陷入惡性循環,而且我國承諾的減排目標都可能會落空。
秦海巖所說的“火電的瘋狂上馬”,在一些煤炭大省尤為典型。比如說山西,在2015年3月環評審批權限下放之后,半年時間之內一口氣新批了20多家煤矸石電廠,完全無視環評審批權限下放之前環保部已經否決過的其中兩個項目。在此前否決其中一個項目的時候,環保部一并對《山西省低熱值煤發電“十二五”專項規劃》提出意見,指出該區域擬新增的這一大批項目“其規模超出了環境容量和水資源承載能力”。
地方“限電”多達八成
可再生能源要花錢買“指標”
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家小風電企業的員工告訴南都記者,2015年9月以來,地方對風電的限制就逐步加劇,“限電”最多的時候達到80%以上。
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一整年的話,該員工告訴南都記者,那就意味著,企業一年只能有2000多萬的收入,但卻要付出2000多萬的運行費用、4個億的銀行還款以及2個億的折舊費用,不僅虧得血本無歸,資金鏈都會斷掉。
當地一位經濟部門的官員告訴南都記者,煤炭行業一直是拉動寧夏經濟增長的“龍頭”。近年來,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自治區政府要求電廠與神華寧煤等煤炭生產企業簽訂“電煤合同”,簡言之,就是火電廠要承諾每年要買夠多少噸煤。“按理說,政府不應該這樣過于干涉市場,但是為了保發展,也沒辦法了。”他說,全區的火電廠保證一年燒掉3000萬噸左右的電煤,政府還按月來考核指標完成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可再生能源的“搶份額”讓他們頭疼不已。該官員告訴南都記者,本來往東部的外送電量就少了,但電網還把青海、甘肅等地沒有消化掉的新能源增加了進去,壓縮了火電外送的比例,“壓了我們十幾億度,這是發改委給我們挖的‘坑’。”
相比于寧夏的棄風限電,云南的“干預措施”顯得更加“簡單粗暴”。2015年11月20日,云南省工信委下發了一份《風電火電清潔能源置換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按照省政府研究緩解云南省火電企業困難有關工作會議紀要的要求,2015年的11月和12月,當云南省的火電廠發電量小于分配給他們的計劃電量時,水電企業和風電企業要將自己發電收益的一部分支付給火電企業作為補償。“相當于你占用了火電的特權指標,就得給人錢作為‘補償’。”一位業內人士對南都記者說。
煤價跌了,火電賺了
改變特權式排序才能根本扭轉
在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看來,中國碳排放達峰值的時間完全可以再提前。他告訴南都記者,2020到2025年之間實現峰值是可能的,“但是不能犯錯誤,現在犯錯誤還不是煤電過多的問題,而是蓋了也不用,過剩浪費了。這就是拿大家的錢花著玩的。”
產業界對改革能源結構也似乎并不是太有動力。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李俊峰告訴南都記者,五大電力公司都有自己的火電,而且是占大頭的板塊,他們保自己的火電就夠了。以前煤價貴的時候,發一度電能賺一毛錢,現在煤價已經從六七百塊錢跌到兩百多塊錢了,發一度電就能賺3毛錢。而且火電有計劃電量,可以優先上網。所以他們就算是把自己的風電全部棄了,那也是賺錢的。
因此,要扭轉這種現象,所謂的“能源革命”必須從頂層設計的改革和整個市場運行規則的調整開始。
卓爾德(北京)環境研究與咨詢中心首席能源經濟師張樹偉告訴南都記者,能源結構的調整,并不應該是一個“分蛋糕”的問題。“很多人會這樣認為:為什么現在風電上不了網?是因為火電不肯讓出它的利益,認為風電分到的‘蛋糕’就是火電減少的———這也是不對的。”
張樹偉說,像在德國等國家,風電和光伏確實也是優先上網,但這種是通過風電本身的競爭特性去保證的。簡單地說,就是它的競價上網機制,有利于風電、光伏這種不需要原料成本的能源獲得優先上網權。
在可再生能源的起步和發展的階段,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也都是給予補貼以支持,補貼的目的并不是因為其“清潔”而“花高價”用它,而是要以行政手段彌補市場失靈的部分。事實上,在德國等國家,風電的成本已經降到了可以直接與火電競爭的程度。而在丹麥、挪威等環境標準特別嚴格的北歐國家,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已經低于火電,并且已經成為了電力市場的主力軍。
在張樹偉看來,中國沒有這樣的排序手段,永遠是特權式的排序,我說你優先你就優先。沒有市場競價的過程。這就是“棄風”“棄光”的主要原因。
但是,最近新出的6個“電改”配套文件也讓他看到了些希望。里面涉及到的如何建立中長期市場和短期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已經是在“試圖做正確的事情”。接下來就是看如何破除舊有的制度和觀念障礙,把事情做好做正確。
如果棄風棄光問題不能盡快解決,可再生能源行業將整體陷入惡性循環,而且我國承諾的減排目標都可能會落空。
———中國風能協會秘書長秦海巖
179個污染天,其中46天重度污染———這是北京市環保局公布的2015年北京天氣狀況。2015年入冬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出現了三次大范圍重污染天氣。12月,環保部緊急向12個省級人民政府印發預警通知,要求啟動應急響應,最大程度減輕污染危害。隨后,全國共有15個城市先后啟動重污染天氣紅色預警,預警級別和范圍均超以往。
根據環保部的研判和總結,煤炭的使用依舊是霧霾的第一大來源。
2015年,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不僅用電需求疲軟,煤炭價格也一直不見起色。但是,產業鏈末端的煤電行業寄托著拉動煤炭消費的熱望和各地GDP的期待,在一個市場化程度不足的電網系統中依然堅守著優勢地位。這時候,很多人也開始熱議———為什么霧霾如此嚴重,能源結構卻這么難調整,可再生的風電、光伏和水電更是大量被棄之不用,造成巨大的浪費?
與減排承諾背道而馳
火電“瘋狂上馬”,“棄風棄光”大面積出現
“中國不僅承受著氣候變化的巨大影響,也面臨著環境污染的嚴峻形勢。因此,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生活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不是別人逼著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就迫切要做的事情。”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在巴黎氣候大會“基礎四國”的發布會上說。
為證明責任感與決心,在巴黎談判的會前和會中,各國元首、部長們紛紛向全世界宣布了各自國家的減排方案。各國已經有了這樣一個共識:導致全球氣候迅速變化的溫室氣體增量主要是由工業化進程中化石能源的使用造成的,因此來一場“能源革命”,大幅度調整能源結構,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最核心的手段。同時,不論是電煤、散燒煤,還是汽車尾氣———這些反復被論證為“霧霾元兇”的,并且在排名先后問題上被爭論得熱火朝天的關鍵詞,也全都是來源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因此,對正處于工業化快速進程中的中國而言,“能源革命”又有了第二層意義———那就是向迫在眉睫的環境污染宣戰。
然而,2015年11月到12月間,各地大面積出現“棄風棄光”的現象。中國風能協會秘書長秦海巖對南都記者說:“這就顯得匪夷所思了———法律規定要保障可再生能源優先上網,全額收購,可到現實中怎么卻處處是反著來的呢?”
他告訴南都記者,去年以來,由于電力的產能過剩以及火電瘋狂上馬,棄風棄光問題越發嚴重。尤其是入冬以來,甘肅、寧夏、黑龍江等地區的棄風棄光比例超過60%,有的地方甚至勒令可再生能源機組停發。全年的棄風棄光電量接近500億千瓦時,直接電費損失近300億元。其中棄風電量可能達400億千瓦時,相當于去年新增風電裝機的全年發電量。也就是說,風電產業一年的新增社會經濟效益全部被浪費了。
他擔心,如果棄風棄光問題不能盡快解決,可再生能源行業將整體陷入惡性循環,而且我國承諾的減排目標都可能會落空。
秦海巖所說的“火電的瘋狂上馬”,在一些煤炭大省尤為典型。比如說山西,在2015年3月環評審批權限下放之后,半年時間之內一口氣新批了20多家煤矸石電廠,完全無視環評審批權限下放之前環保部已經否決過的其中兩個項目。在此前否決其中一個項目的時候,環保部一并對《山西省低熱值煤發電“十二五”專項規劃》提出意見,指出該區域擬新增的這一大批項目“其規模超出了環境容量和水資源承載能力”。
地方“限電”多達八成
可再生能源要花錢買“指標”
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家小風電企業的員工告訴南都記者,2015年9月以來,地方對風電的限制就逐步加劇,“限電”最多的時候達到80%以上。
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一整年的話,該員工告訴南都記者,那就意味著,企業一年只能有2000多萬的收入,但卻要付出2000多萬的運行費用、4個億的銀行還款以及2個億的折舊費用,不僅虧得血本無歸,資金鏈都會斷掉。
當地一位經濟部門的官員告訴南都記者,煤炭行業一直是拉動寧夏經濟增長的“龍頭”。近年來,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自治區政府要求電廠與神華寧煤等煤炭生產企業簽訂“電煤合同”,簡言之,就是火電廠要承諾每年要買夠多少噸煤。“按理說,政府不應該這樣過于干涉市場,但是為了保發展,也沒辦法了。”他說,全區的火電廠保證一年燒掉3000萬噸左右的電煤,政府還按月來考核指標完成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可再生能源的“搶份額”讓他們頭疼不已。該官員告訴南都記者,本來往東部的外送電量就少了,但電網還把青海、甘肅等地沒有消化掉的新能源增加了進去,壓縮了火電外送的比例,“壓了我們十幾億度,這是發改委給我們挖的‘坑’。”
相比于寧夏的棄風限電,云南的“干預措施”顯得更加“簡單粗暴”。2015年11月20日,云南省工信委下發了一份《風電火電清潔能源置換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按照省政府研究緩解云南省火電企業困難有關工作會議紀要的要求,2015年的11月和12月,當云南省的火電廠發電量小于分配給他們的計劃電量時,水電企業和風電企業要將自己發電收益的一部分支付給火電企業作為補償。“相當于你占用了火電的特權指標,就得給人錢作為‘補償’。”一位業內人士對南都記者說。
煤價跌了,火電賺了
改變特權式排序才能根本扭轉
在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看來,中國碳排放達峰值的時間完全可以再提前。他告訴南都記者,2020到2025年之間實現峰值是可能的,“但是不能犯錯誤,現在犯錯誤還不是煤電過多的問題,而是蓋了也不用,過剩浪費了。這就是拿大家的錢花著玩的。”
產業界對改革能源結構也似乎并不是太有動力。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李俊峰告訴南都記者,五大電力公司都有自己的火電,而且是占大頭的板塊,他們保自己的火電就夠了。以前煤價貴的時候,發一度電能賺一毛錢,現在煤價已經從六七百塊錢跌到兩百多塊錢了,發一度電就能賺3毛錢。而且火電有計劃電量,可以優先上網。所以他們就算是把自己的風電全部棄了,那也是賺錢的。
因此,要扭轉這種現象,所謂的“能源革命”必須從頂層設計的改革和整個市場運行規則的調整開始。
卓爾德(北京)環境研究與咨詢中心首席能源經濟師張樹偉告訴南都記者,能源結構的調整,并不應該是一個“分蛋糕”的問題。“很多人會這樣認為:為什么現在風電上不了網?是因為火電不肯讓出它的利益,認為風電分到的‘蛋糕’就是火電減少的———這也是不對的。”
張樹偉說,像在德國等國家,風電和光伏確實也是優先上網,但這種是通過風電本身的競爭特性去保證的。簡單地說,就是它的競價上網機制,有利于風電、光伏這種不需要原料成本的能源獲得優先上網權。
在可再生能源的起步和發展的階段,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也都是給予補貼以支持,補貼的目的并不是因為其“清潔”而“花高價”用它,而是要以行政手段彌補市場失靈的部分。事實上,在德國等國家,風電的成本已經降到了可以直接與火電競爭的程度。而在丹麥、挪威等環境標準特別嚴格的北歐國家,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已經低于火電,并且已經成為了電力市場的主力軍。
在張樹偉看來,中國沒有這樣的排序手段,永遠是特權式的排序,我說你優先你就優先。沒有市場競價的過程。這就是“棄風”“棄光”的主要原因。
但是,最近新出的6個“電改”配套文件也讓他看到了些希望。里面涉及到的如何建立中長期市場和短期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已經是在“試圖做正確的事情”。接下來就是看如何破除舊有的制度和觀念障礙,把事情做好做正確。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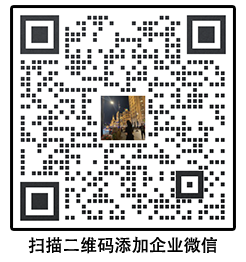









0 條